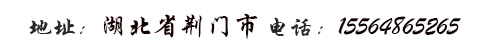基于中药质量标志物QMarker的
|
摘要:鉴于鹿茸质量控制存在基原复杂、品种混乱,质量评价标准匮乏等问题,鹿茸质量控制标准体系建设亟待加强。中药质量标志物(qualitymarker,Q-Marker)的提出及鹿茸中一些相对特异的化学成分逐渐被科学家们发现,为鹿茸质量评价提供了新的契机。详细概括了目前鹿茸质量控制存在的问题,深度辨析了鹿茸Q-Marker的筛选原则,确定其Q-Marker为羟脯氨酸、硫酸软骨素和γ-氨基丁酸,系统构建了鹿茸质量评价标准体系,为推动鹿茸质量控制标准提升和规范鹿业市场提供了保障,有利于鹿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动物药素有“血肉有情之品”的美誉,且多具“行走通窜之功”,自古以来便是医家必备之良药。但由于动物药成分复杂,多数动物药药效物质基础尚不明确,以致动物药的质量控制水平较低、品控指标与药效关联不强问题尤为突出[1]。《中国药典》年版一部共收载动物药50余种,其中仅30种载有鉴定方法,但多以显微和薄层鉴定为主,专属性、特异性较差;仅十几种载有含量测定项;鹿角、鹿角霜、蛇蜕等常用动物药项下无任何鉴定和含量测定方法[2-3]。总体而言,动物药的品质评价、有效成分和药理活性等研究亟待加强。鹿茸系“东北三宝”之一,位居动物药之首,是临床广泛使用的补益类贵细中药材。鹿茸是鹿科动物梅花鹿CervusnipponTemminck或马鹿C.elaphusLinnaeus雄鹿未骨化密生茸毛的幼角,具有壮肾阳、益精血、强筋骨、调冲任、托疮毒的功效[2-3]。《中国药典》年版中收录含鹿药味药品47种;原卫生部药品标准中收录含鹿药味药品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登记含鹿药味药品种,含鹿药味保健食品种。鹿茸每年在中药大品种进出口贸易额中占比超过60%,鹿茸在中药产业及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近年来,随着新西兰赤鹿茸、俄罗斯驯鹿茸等国外大量鱼龙混杂鹿茸源源不断输入国内,中国鹿产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北鹿南引进一步扩大了梅花鹿的养殖范围,道地产区概念逐渐模糊;部分养殖户打着半野生半散养的概念高价销售家养鹿茸。国内鹿茸不规范的养殖、采收、加工、炮制和管理,导致市售鹿茸掺假使假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动摇了鹿茸动物药之首的行业地位。因此规范鹿产业市场已成为行业广泛共识。但一直以来困扰业界最大的难题便是鹿茸的药效物质基础不明确,以何指标评价鹿茸质量尚无定论。数十年来科学家们并未发现鹿茸中的特异性成分,这已然成为影响鹿产业发展“卡脖子”的问题。年刘昌孝院士[4]创新性地提出中药质量标志物(qualitymarker,Q-Marker)的概念,即中药材和中药产品中固有的或加工制备过程中形成的、与中药功能属性密切相关的化学物质,能反映中药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标示性物质,Q-Marker具有中医药理论相关性、特有性、有效性、可测性和传递与溯源性等特征[5-6]。此外,鹿茸中一些相对特异的化学成分逐渐被科学家们发现,这给鹿茸质量评价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因此加快鹿茸质量控制标准体系构建已成为当务之急。本文概括了目前鹿茸质量控制存在的问题,深度辨析了鹿茸Q-Marker的筛选原则,系统构建了鹿茸质量评价标准体系,为鹿茸质量控制标准提升和规范鹿业市场提供了保障,有利于鹿业健康有序发展。 1鹿茸质量控制存在的问题 1.1基原复杂,品种混乱 《中国药典》年版一部中明确规定正品鹿茸的基原为鹿科动物梅花鹿和马鹿雄鹿未骨化密生绒毛的幼角[3],但目前市场上鹿茸的基原混杂,一些伪品充斥市场,包括赤鹿MuntiacusmuntjakZimmermann、驯鹿RangifertarandusLinnaeus、驼鹿AlcesalcesLinnaeus、白唇鹿GervusalbirostrisPrzewalski和水鹿RusaunicolorKerr等,其中尤以赤鹿、驯鹿和驼鹿最多[7]。造成这种乱象的主要原因是鹿科动物物种丰富,包括梅花鹿、马鹿、驯鹿等在内的55种鹿科动物均长有大小、形状不一的鹿角,然而鹿茸的基原鉴别研究滞后。近年来,特异性多聚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chainreaction,PCR)鉴别手段为鹿茸的基原鉴别提供了新思路,魏艺聪等[8]采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建立了基于COI和SRY序列的梅花鹿、马鹿和杂交鹿鹿茸的分析鉴别方法。但鹿茸系高温煮炸、烘烤加工后的中药,DNA在加工过程中受热易降解,易产生假阳性且易受伪品遗传物质的干扰难于鉴别。另一方面,养殖梅花鹿和马鹿品种混乱,良种登记体系不健全。鹿科动物在我国分布广泛,其中梅花鹿包括东北亚种、四川亚种、华北亚种、华南亚种、山西亚种和台湾亚种6个种,马鹿包括天山亚种、塔里木亚种、阿尔泰亚种、东北亚种、阿拉善亚种、甘肃亚种、四川亚种和西藏亚种8个种。家养梅花鹿有地方品种吉林梅花鹿1个种和培育品种双阳、西丰、东丰、四平、东大、敖东、兴凯湖梅花鹿7个,这些品种大多具有遗传性能稳定、产茸性能高的特点[1]。但近年来,不规范的引种、繁育、杂交,不透明的鹿种交换,不健全的良种登记体系,致使大部分品种及品系已失去传统的遗传特性,梅花鹿养殖业面临无种可用的窘境。更有甚者,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枉顾政策法规,钻质量评价标准体系不完善的漏洞,私自将梅花鹿和马鹿杂交,严重影响了鹿茸遗传品质的稳定性。1.2引种和饲养管理不规范 民国时期《增订伪药条辨》中明确记载:“鹿茸……东三省产及青海、新疆均佳。须颜色紫红明润有神,顶圆如馒头式者佳”。《药物出产辨》亦载:“鹿茸产中国边境,长白山为最佳,关东亦佳”。因此,自古以来东三省尤其是长白山地区便是公认的鹿茸道地产区。但近年来,全国各地大力发展中药材人工栽培、驯养和引种,由于未充分考虑药材的道地性和药用植物、动物生长环境(气候、温度、光照等因素)的适宜性,致使一些伪劣品进入中药材市场。这些伪劣品严重影响了中药质量和临床疗效,损害了中药声誉,是影响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梅花鹿和马鹿经过长期的人工驯化已最大程度适应圈养环境,但其目前仍是半驯化家养动物。不科学的圈舍结构、不规范的饲养管理仍会造成鹿茸生产性能降低,品质下降。与此同时,梅花鹿和马鹿在饲养过程中受布鲁氏杆菌、结核杆菌等多种病原微生物的困扰,致使四环素等抗生素被广泛使用,抗生素的滥用进一步增加了鹿茸中的风险因子;在摸清鹿茸生茸机制是孕酮与雄激素相互拮抗调控的基础上,不少养殖户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在二茬茸生长阶段非法使用醋酸氯地孕酮等激素拮抗雄性激素和孕酮,抑制组织骨化,增加二茬茸产量[9],但这种激素催生的二茬茸成分和功效与正常二茬茸是否一致未见报道,非法使用的激素在二茬茸中的残留量及对人体的危害尚不明晰。1.3采收、加工和炮制够不科学 1.3.1采收传统鹿茸采收采用的是人工吊圈的方式,即以物理器械对梅花鹿和马鹿进行固定后直接锯取鹿茸,吊圈收茸费时费力且易造成鹿茸及动物损伤。近年来,考虑到动物福利等因素,目前国内大部分鹿场均采用先麻醉后锯茸的方式采收鹿茸,黄胜广等[10]报道了盐酸赛拉嗪等麻醉剂在鹿茸中的残留,但其对鹿茸功效及安全性的影响未见报道,究竟应当采取何种方式采收鹿茸有待进一步研究。 1.3.2加工目前主产区最常采用的初加工方法仍然是热水煮炸法。热水煮炸法是一种传统的鹿茸产地初加工技术,包括水煮、烘烤、风干等步骤,重复多次直至干燥。煮炸能有效消除鹿茸中的病原微生物,使茸头饱满有型、茸皮光鲜亮丽,但煮炸过程繁琐且耗时较长,稍有不慎易造成茸皮破裂、茸头干瘪等问题,影响成品茸品质[11]。近年来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个别企业采用冷冻干燥技术生产冻干茸,冻干技术能实现快速干燥且最大程度地保留鹿茸中的成分,但其也易保留茸体内的病原微生物,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此外,根据消费者需求的不同,排血茸和带血茸也是常见的产地初加工方式。本课题组前期对比分析了不同加工方式鹿茸中蛋白质、氨基酸、脂肪酸、矿质元素、多糖、胶原蛋白、硫酸软骨素、核苷、生物胺等成分含量差异发现,不同加工方式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鹿茸中的上述成分[12-20]。但不同加工方式对鹿茸药理作用及临床疗效的影响未见报道,有待进一步研究。 1.3.3炮制《中国药典》年版一部收载的鹿茸炮制品包括鹿茸粉和鹿茸片2种,鹿茸粉系鹿茸直接劈成块后研成细粉,鹿茸片炮制工艺相对复杂,具体工艺如下:鹿茸燎去茸毛,刮净,以布带缠绕茸体,自锯口面小孔灌人热白酒,并不断添酒,至润透或灌酒稍蒸,横切薄片,压平,干燥[3]。目前市面多以鹿茸片形式流通和使用,鹿茸片又根据鹿茸切制部位不同分为蜡片、粉片、纱片和骨片,不同部位鹿茸价格差异几十倍乃至上百倍。本课题组分析了不同炮制品及不同部位鹿茸中化学成分含量差异发现,与鹿茸粉相比,鹿茸片中脂肪酸、矿质元素等含量未见减少,多糖、核苷等成分略有减少;蜡片比其他部位含有更多的蛋白质、氨基酸、硫酸软骨素等成分[12-19,21]。此外,目前市场上还存在鹿茸超微粉、鲜鹿茸片等多种商品规格,规范鹿茸炮制工艺及商品等级势在必行。 1.4包装规格、储运条件不明确 鹿茸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油脂,存储不当极易腐败变质,现代冷链仓储及物流为鹿茸的保存提供了便利。但部分养殖户无意识地将新鲜鹿茸、鹿副产品等与成品鹿茸共同存储,容易造成微生物污染等问题。本课题组曾抽取市售鹿茸中微生物含量检测发现,鹿茸中大肠杆菌等微生物含量超标现象普遍,系不规范加工、储运等因素导致。因此明确鹿茸及其制品包装规格、储运条件对保障鹿茸品质及安全具有重要意义。1.5质量评价体系不完善,产业支撑不足 《中国药典》年版鹿茸项下无检查和含量测定项,鉴别项下仅采用茚三酮、斐林试剂定性检测氨基酸和还原糖,薄层色谱法以甘氨酸对照品和鹿茸对照药材在相应位置显相同颜色斑点为鉴别标准,无特异性指标成分,专属性差[3]。该标准自《中国药典》年版收载且一直沿用至今,40多年一直未作修订和补充,已不能适应当下快速发展的产业需求。鹿茸质量控制指标成分的缺失和质量标准体系的不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市售鹿茸掺假使假现象的发生,严重阻碍了鹿业的深度发展。此外,话语权最重的国家标准中没有鹿茸质量评价标准,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等单位负责起草的国家标准《梅花鹿茸分等质量》《马鹿茸分等质量》《鹿茸加工技术规程》3项国家标准已通过国家标准委批复,待发布实施。在现行的其他标准中,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DB22/T-和T/CACM.58-均以外观性状为依据进行品质等级划分;NY/T-和DB22/T-以水分、钙、氨基酸、重金属和微生物作为限量指标。这些标准普遍存在标准覆盖范围窄、质量评价指标专属性差且不合理、重金属和微生物含量限量标准不一致等问题,鹿茸药材质量控制成分筛选和品质评价标准亟待提高。1.6市场监督管理缺位 梅花鹿和马鹿属于野生动物(家养梅花鹿和马鹿属于特种家养畜禽),归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和农业农村部监管;在梅花鹿养殖主产区吉林省,归畜牧业部门监管。对于第二产业来说,鹿茸、鹿角属于药品原料,归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监管;鹿胎、鹿骨属于保健食品原料,归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监管;鹿肉、鹿筋属于食品原料,归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司等部门监管;鹿皮可以制作服饰,归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监管。因此鹿是一个典型的多头管理的产业,多头管理、监管责任不清及质量评价体系不完善导致鹿茸市场监督管理存在缺位。对生产管理的不重视,导致品质较差的老鹿、病鹿和淘汰鹿鹿茸及鹿制品流入市场;滥用麻醉剂、增茸素、抗生素及重金属超标等问题屡屡发生。上游生产管理的缺位导致中下游中药材、中药饮片和中成药产品质量堪忧,同时也限制了鹿皮、鹿尾、鹿鞭、鹿胎等鹿副产品的精深开发和利用。总而言之,鹿茸质量控制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其中基原复杂、品种混乱,质量评价标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尤为突出。鹿茸质量控制标准体系建设任重而道远。2基于“五原则”的鹿茸Q-Marker辨识分析 Q-Marker由刘昌孝院士于年创新性地提出,即中药材和中药产品中固有的或加工制备过程中形成的、与中药功能属性密切相关的化学物质,能反映中药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标示性物质。Q-Marker需同时满足中医药理论相关性、特有性、有效性、可测性和传递与溯源性5大基本原则[22-26]。基于“五原则”的Q-Marker辨识分析对鹿茸Q-Marker的筛选具有重要意义。2.1鹿茸中Q-Marker的有效性 有效性是Q-Marker的核心要素,有效性主要体现在药性、药效和入血成分及其代谢产物等。鹿茸始载于《神农本草经》,位列中品,谓:“鹿茸味甘,性温……主漏下恶血,寒热惊痫,益智强智,生齿不老”,历代本草及药典中均有收载。《中国药典》年版鹿茸项下描述包括“味甘、咸;归肾、肝经;具有壮肾阳,益精血,强筋骨,调冲任,托疮毒的功效,主治肾阳不足,精血亏损,阳痿滑精,宫冷不孕,羸瘦,神疲,畏寒,眩晕,耳鸣,耳聋,腰脊冷痛,筋骨痿软,崩漏带下,阴疽不敛”[3]。通过对古籍及《中国药典》的考察不难发现,药性方面,鹿茸性温,具有补肾壮阳之功效,鹿茸可以通过兴奋下丘脑-垂体-性腺内分泌轴使血液中性激素含量升高。味甘、咸,甘味系其中丰富的多糖、氨基酸等成分,与调节机体免疫力、抗骨质疏松等药理功能密切相关;咸味系其中的矿质元素,具有抗菌、抗炎等功效。归肾、肝经,具有壮肾阳功效的鹿茸入肾经,符合中医认为肾主生殖的理论[27]。药效方面,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鹿茸具有抗骨质疏松、抗衰老、抗氧化、抗疲劳、抗肿瘤、抗抑郁、抗肝损伤、增强记忆力、提高机体免疫力及性激素样作用等多种药理活性[28-35]。吕经纬等[36]通过网络药理学研究获得了鹿茸中的17β-雌二醇、氨基葡萄糖、雌酮、D-葡萄糖醛酸等14个成分及个靶点,发现了甲状腺受体相互作用蛋白2、腺苷酸环化酶1型等26个关键靶点蛋白,进一步揭示了鹿茸在治疗骨质疏松和抗肿瘤方面具有潜在的优势。 然而,鹿茸中入血成分及其代谢产物的研究相对较少,Yu等[37]通过体外模拟鹿茸胃肠道消化反应,采用LC-MS/MS鉴定分析了鹿茸水提物、胃液消化物和胰液消化物中23、、个肽段,研究表明胶原蛋白是鹿茸中的主要蛋白质,在胃消化物中释放了34种多肽,在胰消化物中释放了种多肽。关于鹿茸中入血成分及其代谢产物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2.2鹿茸中Q-Marker与中医药理论的相关性 中药配伍是中医药理论的核心内容,中药配伍后能显著影响药效物质基础与作用机制,同一药材在不同处方中以“君、臣、佐、使”发挥不同的药效[26]。Q-Marker的筛选要求延伸到临床应用层面,应基于中药临床应用最终效应成分及其功效的临床表达形式确定Q-Marker。林贺等[38]系统整理了自汉至清的中医药典籍发现,中医药古籍和传统方剂中含鹿茸的方剂包括余首,充分扮演了“君、臣、佐、使”的角色,鹿茸用量在1分~2斤8两,大部分用量在2钱~4两,用法上常与肉苁蓉、菟丝子、附子、当归、牛膝、人参、五味子等配伍使用,发挥壮肾阳、益精血、强筋骨之功效。鉴于中药方剂“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鹿茸中Q-Marker的筛选需充分考虑其配伍环境,一方面应与鹿茸“壮肾阳、益精血、强筋骨”的临床疗效密切相关,另一方面鹿茸中的Q-Marker含量应相对较高,避免其在复方中用量较低时难于检测。2.3鹿茸中Q-Marker的特有性 特有性是中药鉴别、质量控制和评价的核心,具有专属性,主要体现在2个层次:(1)能代表和反映同一类药材的共有性并区别于其他药材的特征性成分;(2)能反映同一类、不同种药材之间的差异性成分[25]。鹿茸Q-Marker特有性的内涵包含系统演化、亲缘关系学、生物学特性和特异性成分等,又与道地产区,不同形态、生长阶段和产地初加工方式等密切相关。2.3.1鹿茸的共性及区分于其他物种的特异性 (1)基于系统演化和亲缘关系学分析的鹿茸Q-Marker筛选:《中国药典》年版一部中明确规定鹿茸基原为鹿科动物梅花鹿和马鹿雄鹿未骨化密生绒毛的幼角[3],但目前市场上鹿茸基原混杂,大量伪品充斥市场,主要包括赤鹿茸、驯鹿茸和驼鹿茸。由于遗传物质的差异,不同物种形态及化学成分均会表现出差异,最终影响中药的疗效。 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为鹿科动物系统演化和亲缘关系分析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手段,鞠妍等[39]以线粒体DNA序列差异为依据分析了鹿科动物的系统进化关系(图1),研究表明以线粒体DNA为依据能将梅花鹿、马鹿、驯鹿、驼鹿等20多种鹿科动物系统分为鹿亚科、麂亚科、空齿鹿亚科和獐亚科,其中梅花鹿和马鹿为亲缘关系最近的姐妹群,并能与驯鹿、驼鹿等明显区分开。贾静等[40]以DNA条形码对71份市售鹿茸粉药材进行鉴定,其中38%为《中国药典》年版规定的基原,62%为其他基原,以驯鹿为主。截止目前,《中国药典》年版中采用PCR法进行基原鉴别的药材包括蕲蛇、乌梢蛇和川贝母[3],应用DNA分子鉴别中药基原得到了业界广泛的认可,《中国药典》中将PCR法应用于中药基原的鉴别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以分子生物学技术筛选梅花鹿、马鹿中的特异性DNA片段构建鹿茸基原的鉴别方法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此外,在物种遗传物质不同的基础上,其调控体内所表达的蛋白质等具有高度特异性。《中国药典》年版采用液质联用的方法分析阿胶、龟甲胶和鹿角胶中特异性肽段,进而控制中药基原[3]。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最新的研究表明,梅花鹿茸、马鹿茸和驯鹿茸中有明显的特异性多肽,可以通过主成分和偏最小二乘法等分析方法进一步筛选、鉴别[41]。 (2)生物学特性结合化学成分分析的鹿茸Q-Marker筛选:药用植物能够在体内通过乙酸-丙二酸途径、甲戊二羟酸途径、莽草酸途径、氨基酸途径及其复合途径等生源途径代谢产生苯丙素类、醌类、黄酮类、萜类和生物碱类等成千上万的次生代谢产物,其在植物中的生成和分布通常具有种属、组织器官和生长发育期的特异性[42]。对药用植物次生代谢产物及其生源途径特异性分析有助于Q-Marker的筛选。然而,动物药中通常无特异性次生代谢产物,次生代谢产物代谢路径研究少且不深入导致动物药中Q-Marker的筛选较为困难。但鹿茸因其由软骨组织发育且具有周期性脱落等独特的生物学特性(图2),为鹿茸中Q-Marker的筛选提供了较好的切入点[43]。 首先,鹿茸为典型的动物药,胶原蛋白是动物异于植物的重要结构蛋白,主要存在于动物结缔组织(皮肤、肌肉)、骨骼、软骨等,具有促进伤口愈合、润滑关节等功能[43-46]。其中羟脯氨酸是构成胶原蛋白的特异性氨基酸,不参与其他蛋白质的合成,系胶原蛋白合成过程中已合成肽链中的脯氨酸被羟化酶转化而成。《中国药典》年版采用异硫氰酸苯酯柱前衍生HPLC法对阿胶、龟甲胶和鹿角胶中羟脯氨酸进行含量测定,并对3种胶类中药中羟脯氨酸含量提出限量标准[3]。本课题组采用氨基酸自动分析仪对鹿茸中羟脯氨酸进行含量测定发现,梅花鹿茸和马鹿茸中均能检出羟脯氨酸且含量差异不显著,不同加工和炮制方式鹿茸中羟脯氨酸含量最低为2.49%[14]。其次,鹿茸不同于其他动物药,系软骨组织发育而来,硫酸软骨素是高等动物软骨组织中特有的酸性黏多糖,具有抗关节炎、抗骨质疏松和抗肿瘤等生物学活性[47-49],能够部分代表鹿茸的临床疗效,是鹿茸中相对特异的化学成分。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鹿茸中硫酸软骨素存在形式以硫酸软骨素A、B和C为主,梅花鹿茸和马鹿茸中均能检出硫酸软骨素且含量差异不显著,不同部位和规格鹿茸中硫酸软骨素含量存在显著差异,鹿茸中硫酸软骨素质量分数最低为mg/kg,鹿角仅为mg/kg[19,50]。吕经纬等[36]通过网络药理学研究发现,鹿茸中硫酸软骨素的重要组成单元氨基葡萄糖能够协同其他多个化学成分通过腺苷酸环化酶1型等10个关键靶点作用于癌症信号通路,提示氨基葡萄糖具有抗肿瘤和增强免疫力的作用。因此,以生物学特性、化学成分特异性、药效物质基础和药理作用为考量因素,硫酸软骨素是鹿茸中Q-Marker的不错选择。此外,鹿茸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哺乳动物中唯一可再生的器官[43],其中含有丰富的血管、神经等组织,γ-氨基丁酸是一种非蛋白组成氨基酸,在哺乳动物中仅存在于神经组织中,具有抗疲劳、促睡眠等作用[51-54]。本课题组对鹿茸、鹿角、鹿角霜及鹿角胶等鹿制品中γ-氨基丁酸进行含量测定发现,梅花鹿茸和马鹿茸中均能检出γ-氨基丁酸,且含量差异不显著,鹿茸中γ-氨基丁酸质量分数最低为mg/kg,鹿角中γ-氨基丁酸显著低于鹿茸,为mg/kg,鹿角霜中几乎不含γ-氨基丁酸[55]。γ-氨基丁酸广泛存在于植物、动物及微生物中,作为鹿茸中Q-Marker特异性较差,但可以考虑以γ-氨基丁酸含量为辅结合其他化学成分综合评价鹿茸质量。最后,鹿茸奇特的生物学特性还包括周期性的脱落与再生,鹿茸在春季萌生,初秋长成后褪去茸皮变成鹿角,用于交配中竞争配偶,鹿角于冬季或早春脱落。现代研究表明,鹿茸的生长和再生与动物体内性激素水平密切相关,孕酮和雄激素相互拮抗调节鹿茸的发生、生长、骨化和脱落[8]。激素的生理功能也与鹿茸“补肾阳,调冲任”的功效密切相关。李春燕等[56]建立了鹿茸中18种性激素的提取技术。Lu等[57]采用GC-MS法测定了不同产地鹿茸中18种激素含量,发现不同产区及部位鹿茸中性激素含量差异显著。激素作为鹿茸中Q-Marker具有一定的特异性,但因激素具有微量、高效的特点,其在鹿茸及鹿制品中含量低且难于检测,鹿茸以贵细药材在中药复方中少量使用时更加难于检测。综上所述,基于系统演化和亲缘关系学分析的DNA及特异性肽段为鹿茸基原真伪的鉴别提供了保障,生物学特性结合化学成分分析的羟脯氨酸、硫酸软骨素、γ-氨基丁酸和激素等多指标相结合的Q-Marker为鹿茸质量控制提供了新的思路。2.3.2不同鹿茸种内的特异性 (1)不同基原鹿茸特有性:宋代《梦溪笔谈》记载:“鹿茸利补阴。凡用茸,无乐太嫩,世谓之茄子茸,但珍其难得耳,其实少力,坚者又太老,唯长数寸,破之肌如朽木,茸端如玛瑙、红玉者最善”。说明古代本草记述的鹿茸和现今所用的梅花鹿茸相吻合。梅花鹿茸为主流品种,历史悠久,马鹿与梅花鹿同属且亲缘关系近,但本草文献中少有记载,有学者认为马鹿茸在我国被应用至少有二三百年以上的历史,有关梅花鹿茸和马鹿茸药理活性差异的报道较少。 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能够实现梅花鹿茸和马鹿茸的鉴别。魏艺聪等[8]建立了基于COI和SRY序列的梅花鹿、马鹿和杂交鹿鹿茸的分析鉴别方法,该方法稳定、可靠,能用于梅花鹿、马鹿和杂交鹿鹿茸的鉴别。地方标准DB22/T-也建立了PCR鉴别梅花鹿、马鹿茸片的方法。本课题组对梅花鹿茸和马鹿茸中蛋白质、氨基酸、脂肪酸、矿质元素、核苷、硫酸软骨素、生物胺等化学成分进行了系统研究及分析,未发现二者有显著性差异[58]。杨秀伟等[59-60]研究表明,梅花鹿茸中次黄嘌呤含量较马鹿茸低,但梅花鹿茸对单胺氧化酶的抑制作用比马鹿茸高2倍。(2)不同形态鹿茸化学成分特有性:《本草图经》载:“鹿茸……今有山林处皆有之、四月角欲生时,取其茸,阴干,以形如小紫茄子者为上。或云茄子茸太嫩,血气犹未具,不若分岐如马鞍形者有力。茸不可嗅,其气能伤人鼻”。《本草图经》插图(图3)中鹿茸呈茄子形,又无分叉等形态,结合文中“形如小紫茄子”“马鞍形者有力”等描述,可见历代沿用的鹿茸与今商品鹿茸的梅花鹿二杠茸相吻合。 《中国药典》年版收载的不同形态鹿茸包括梅花鹿二杠茸、三岔茸和马鹿三岔茸、四岔茸[3],此外,梅花鹿初次生长的毛桃茸也在市场上广泛流通。同一鹿茸药材,不同形态之间化学成分的差异是Q-Marker特有性的重要体现。本课题组前期对梅花鹿毛桃茸、二杠茸和三岔茸中蛋白质、氨基酸、脂肪酸、矿质元素、多糖、生物胺、核苷、硫酸软骨素等化学成分进行了系统的含量测定及分析,发现不同形态鹿茸中硫酸软骨素、氨基酸等9类成分均呈现出二杠茸含量最高,三岔茸其次,毛桃茸含量最低的规律[61]。原因可能是毛桃茸源于未成年雄鹿,其生长发育不完全,营养物质率先满足身体生长发育所需不能为鹿茸的生长提供充足的养分,因此毛桃茸上述成分含量较低。由此可见,借助特异性化学成分Q-Marker的含量测定能够将不同形态鹿茸进行区分。(3)不同生长阶段鹿茸化学成分特有性:马鹿鹿角或鹿角脱盘于每年2、3月份脱落,之后进入快速生茸阶段,马鹿茸1年通常只采收1茬;梅花鹿鹿角或鹿角脱盘于每年4月份脱落,若采收及时,梅花鹿鹿茸1年可采收2茬,但二茬茸茸型及品质较差。梅花鹿头茬茸和二茬茸在《中国药典》年版中均有收载[3],然而暂无文献报道头茬茸和二茬茸在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和临床疗效等方面的差异。本课题组通过对梅花鹿头茬茸和二茬茸中9类化学成分研究发现,头茬茸中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脂肪酸和核苷4类化合物含量显著高于二茬茸[62]。希望未来能够借助特异性化学成分Q-Marker的含量差异将不同生长阶段鹿茸进行区分。 (4)不同产地初加工方式鹿茸化学成分特有性:适宜的产地初加工及炮制方法是保证中药药效的基础,市售鹿茸根据产地初加工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煮炸茸、冻干茸、排血茸和带血茸,《中国药典》及各级标准中均未明确规定鹿茸的产地初加工方式,导致养殖户以客户要求为由任意加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鹿茸的品质。本课题组围绕不同加工方式鹿茸中化学成分差异做了大量的工作,系统分析了不同加工方式鹿茸中蛋白质、氨基酸等9大类成分中百余个组分发现,不同产地初加工方式对鹿茸中化学成分含量影响显著,冻干茸对蛋白质、氨基酸、脂肪酸等的保留优于煮炸茸,带血茸对蛋白质、氨基酸、矿质元素等的保留显著优于排血茸[12-19]。 此外,虽然在外观上冻干茸易于与煮炸茸区分,但切片、粉碎后难于分辨。本课题组建立了鹿茸中美拉德反应产物标志性成分5-羟甲基糠醛(5-hydroxymethylfurfural,5-HMF)、羧甲基赖氨酸、羧乙基赖氨酸和糠氨酸等分析方法,通过对不同加工方式鹿茸中上述成分含量测定发现,煮炸茸中5-HMF等美拉德反应产物显著高于冻干茸,带血茸显著高于排血茸[63-65]。导致上述结果的原因为鹿茸热加工过程中高温加剧了美拉德反应产物产生更多5-HMF等物质,带血茸中富含能发生美拉德反应的氨基化合物和羰基化合物,其易反应生成更多5-HMF等物质。未来期望在规范鹿茸产地初加工标准方法的基础上筛选不同加工方式鹿茸中Q-Marker,加强对鹿茸产地初加工的监管和检查。2.4鹿茸中Q-Marker的可测性 Q-Marker的可测性是基于点-线-面-体的质量控制模式建立的中药多元质量控制方法,包括指标成分、指示性成分、类成分和全息成分[26]。指标成分能反映中药的特异性、区别于其他药材的功能属性,是评价中药质量优劣和合格限度的“金标准”。考虑到鹿茸的构效关系及功效发挥多靶点、多途径的特点,硫酸软骨素、羟脯氨酸等成分十分契合指标成分的筛选原则,在此基础上需建立γ-氨基丁酸等相结合的多指标含量测定方法。指示性成分系中药中含量大、功效类似的代表性成分。目前NY/T-和NY/T-采用氨基酸自动分析仪对鹿茸中17中氨基酸进行含量测定,进而评价其质量。鉴于氨基酸自动分析仪对氨基酸分析的普适性,建议增加羟脯氨酸和γ-氨基丁酸等特异性指标,加强对鹿茸质量控制的科学性、合理性。 类成分指结构相似的一类成分。不同于人参等植物药可用总皂苷等类成分对其总体功效进行评价,鹿茸中无结构明晰、功能明确的类成分。鉴于课题组前期研究成果,现阶段建议以总蛋白、总多糖、总脂肪酸、总灰分等指标在“面”的层面对鹿茸质量进行控制。全息成分是在所用分析方法下显现成分及其理化和波谱学信息,指纹图谱技术是常用的基于全息成分的模式识别方法,目前多用于评价质量的一致性。孙伟杰等[66]建立了鹿茸中6种核苷类成分的指纹图谱,该方法对鹿茸饮片质量控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2.5鹿茸中Q-Marker的传递与溯源性 2.5.1鹿茸不同炮制品中Q-Marker的传递与溯源性《中国药典》年版中收载的鹿茸炮制品包括鹿茸粉和鹿茸片,本课题组分析了鹿茸不同炮制品中化学成分含量差异发现,鹿茸粉与鹿茸片中均能检测到前文多次提到的鹿茸中Q-Marker的备选成分硫酸软骨素、羟脯氨酸、γ-氨基丁酸等,体现了鹿茸中Q-Marker由中药材向中药饮片的传递与溯源性,但与鹿茸粉相比鹿茸片中多糖、核苷等成分略有减少[21,50,67]。 2.5.2鹿茸不同饮片切制部位中Q-Marker的传递与溯源性鹿茸片是市售鹿茸的主要流通形式,根据饮片切制部位的不同又被分为蜡片、粉片、纱片和骨片。本课题组对不同部位鹿茸中化学成分含量进行了细致的比对分析,发现不同部位鹿茸中化学成分含量差异明显,蜡片中蛋白质、氨基酸等含量显著高于其他部位,其他部位无明显差异;不同部位鹿茸中硫酸软骨素和糖类物质表现出蜡片含量最高,粉片、纱片和骨片含量依次递减的规律;不同部位鹿茸中矿质元素(尤其是钙和镁)呈现出蜡片含量最低,粉片、纱片和骨片含量依次增高的规律[12-19]。鹿茸系软骨组织分化而来,越靠近顶部分生组织越活跃,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物质越丰富;基部逐渐钙化,钙、镁等矿质元素含量逐渐增加。不同饮片切制部位鹿茸中化学成分差异性分布是Q-Marker传递与溯源性的体现。 2.5.3不同鹿制品中Q-Marker的传递与溯源性《中国药典》年版一部收载的鹿制品包括鹿茸、鹿角、鹿角胶和鹿角霜[12-19]。鹿茸系幼嫩的软骨组织,若不及时采收组织骨化后便形成鹿角,采收后的角基于次年春季脱落形成鹿角脱盘。鹿角胶系鹿角或鹿角脱盘经粉碎、熬制、浓缩而成的胶块,鹿角霜系鹿角胶熬制后剩余的残渣。整体而言,鹿制品的质量控制标准均相对匮乏,鹿茸及鹿制品的质量控制标准亟待提高。本课题组曾对不同鹿制品中的硫酸软骨素、羟脯氨酸和γ-氨基丁酸含量测定发现,不同鹿制品中上述成分含量差异显著,鹿茸中硫酸软骨素含量最高,鹿角胶中羟脯氨酸含量最高,鹿角和鹿角霜中γ-氨基丁酸含量最低[50,55,67]。鹿茸、鹿角、鹿角胶和鹿角霜均是鹿茸生长不同阶段的产物及制品,不同鹿制品中化学成分含量差异是Q-Marker传递与溯源性的体现,硫酸软骨素、羟脯氨酸和γ-氨基丁酸在不同鹿制品中的差异分布是其具备作为鹿茸中Q-Marker备选的良好体现。 综上所述,鹿茸由软骨组织发育而来,其中富含丰富的血管和神经组织,硫酸软骨素、羟脯氨酸和γ-氨基丁酸等是其中相对特异性的化学成分(特有性),具有抗关节炎、抗骨质疏松、抗疲劳等生物活性(有效性),与中医药理论认为的“壮肾阳、强筋骨”等功能主治非常吻合(中医药理论相关性),在鹿茸饮片及炮制品中均能被检测到(可测性、传递与溯源性),符合Q-Marker的5大基本原则。3构建鹿茸质量控制标准体系 3.1生产全过程质量控制体系建立 年6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的《中药质量控制研究技术指导原则》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中药材源头质量控制,对中药材种质种苗、种植养殖、采收加工、包装贮藏等环节进行生产全过程质量控制。具体到鹿茸生产过程中需从种质品种、养殖管理、采收加工、包装贮藏和质量评价5个环节进行全过程质量控制(图4)。3.2鹿茸质量控制标准体系 3.2.1鹿茸分等分级质量标准鹿茸分等分级质量标准系根据鹿茸茸型、感官、质量等基础指标为依据将鹿茸划分为一等茸、二等茸、等外茸等不同等级的质量评价标准,涵盖了梅花鹿茸、马鹿茸,鲜鹿茸、干鹿茸,锯茸、砍茸,初生茸、再生茸和二杠、三岔等不同形态鹿茸,见图5。 3.2.2鹿茸加工炮制技术规程产地初加工及炮制方法能影响鹿茸中化学成分含量进而影响药效,规范鹿茸产地初加工及炮制方法势在必行。按照目前市场主流的鹿茸产地初加工及炮制方式,需制订《排血茸加工技术规程》《带血茸加工技术规程》《煮炸茸加工技术规程》《冻干茸加工技术规程》4项鹿茸产地初加工技术规程,制订《鹿茸炮制规程》《鹿茸切制规程》等炮制技术标准。 3.2.3鹿茸包装、贮藏及运输技术规范鉴于鹿茸制品易受微生物污染等问题,需进一步规范鹿茸包装、贮藏及运输等环节,建立《鹿茸包装、贮藏及运输技术规范》,从中间环节保证鹿茸化学成分及药效不受影响。 3.2.4鹿茸提取物及标准汤剂指纹图谱鹿茸为补益类贵细药材,在中成药制剂过程中往往在靠后工艺流程中添加,但鉴于Q-Marker传递和溯源性的要求及配方颗粒等新型中药剂型的发展,未来发展鹿茸提取物可能存在相当大的空间。建立《鹿茸提取物》及《鹿茸标准汤剂指纹图谱》对规范中成药生产企业及市场流通、监管具有重要意义。 3.2.5规范鹿茸中Q-Marker和风险因子检测方法含量测定的准确性离不开检测方法的重复性、稳定性和科学性。本课题组在参考《中国药典》年版二部硫酸软骨素钠、硫酸软骨素钠片、硫酸软骨素钠胶囊中硫酸软骨素含量测定方法的基础上,建立了鹿茸中硫酸软骨素的含量测定方法;在参考NY/T-的基础上,建立了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测定鹿茸中羟脯氨酸含量的方法;在参考NY/T-的基础上,建立了柱前衍生UPLC法测定鹿茸中γ-氨基丁酸含量的方法。在此基础上,需进一步规范形成《鹿茸中硫酸软骨素含量测定方法》《鹿茸中羟脯胺酸含量测定方法》《鹿茸中γ-氨基丁酸含量测定方法》等行业标准或团体标准,为鹿茸中Q-Marker的检测提供保障。 近年来,风险因子监控逐渐受中药监管部门的重视,《中国药典》年版征求意见稿中广泛增加了重金属和农药残留在植物药中的限量标准。动物药方面,仅有水蛭等个别品种规定了重金属限量标准,DB22/T-中规定了鹿茸中重金属限量标准但有待商榷。鉴于风险因子的重要影响,鹿茸质量控制标准体系需建立《鹿茸中重金属的检测方法和限量标准》《鹿茸中麻醉剂的检测方法和限量标准》《鹿茸中增茸素的检测方法和限量标准》和《鹿茸中兽药残留的检测方法和限量标准》等风险因子标准检测方法和最高残留量。 4结语 虽然目前鹿茸质量控制标准研究还存在许多问题和短板,但近年来鹿茸质量控制成分筛选及质量标准体系建设逐渐受到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uanshens.com/wsszz/9252.html
- 上一篇文章: 定州人防忽悠,这些药便宜但效果一样好
- 下一篇文章: 端午前后特别要警惕它被咬一口轻则昏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