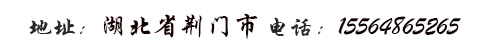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小说丨李庆忠扶贫小调
|
扶贫小调 李庆忠 一 黄家义心急火燎地赶到现场时,骡子已经死在地里硬翘翘的。一群嗜臭的苍蝇们围着骡尸兴奋地飞。地角的核桃树上集聚了十数只蠢蠢欲动的老鸹,要不是忌惮人的存在,早就飞冲过来争抢大餐。 现场有五人,连赶到的黄家义是六个。宋依芬沮丧地坐在开满风雨花的地埂上,手不知所措地揉碾着身边的野草,半背篮没有撒完的化肥撂在地里,压断了两棵已经长到筷子高的烟苗。两个派出所民警蹲在死骡边上核实死因。村委会主任老金皱着眉站在地边吸烟。还有一个是宋依芬丈夫的大哥胡大栓,站在死骡边上喋喋不休。 黄干部你说咋办?你要对死骡负责。胡大栓冲刚到现场的黄家义开腔。 都怪我大意,让骡嘴够得到化肥口袋。宋依芬抱怨自己。 是牲口蠢,连氢氨都敢吃,不闹死才怪!老金说。 这化肥是你送来的扶贫物资吧?胡大栓还是盯着黄家义,话里有话。 化肥是我买的,不是黄大哥!宋依芬又抢了胡大栓的话。 冇哄鬼,我亲眼看见他昨天往你家搬。胡大栓说。 他送的是尿素,闹骡的是氢胺。宋依芬说。 胡大栓不再言语,脸上有些无趣。 黄家义站在地里一直不吭气,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真他妈砍竹子偏逢节疤。离开现场回到村委会,老金抱怨了一声。 化肥是我送给她家的。我负全责。黄家义坚定地说。 你说你买的,宋依芬说她买的?到底咋回事?老金有些纳闷。 尿素和氢氨都是我买的。黄家义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你咋负责?你去给她家当骡子用!以身赎罪!老金冲着黄家义开玩笑。 这主意不错,白天你犁地,晚上你犁人。同去驻村的单位同事刘小展体会不到一个大牲口的死对一个农户的严重性,一边在电脑上录数据一边冒出了句荤话。 扶贫是重大政治任务。讲不得啷当话。黄家义苦笑着说。 我买匹骡子还她。黄家义说。 哦,地里的死骡咋处理?黄家义突然想起骡子的后事。 埋了,埋了,要不……算了,找个给收残牛残马的来,好歹百八十块钱卖得。老金犹豫了一下说。 嗯,行!那老金你联系,我去料理。黄家义自告奋勇地离开了村委会。 二 黄家义实在没想到他的结对帮扶对象里会有宋依芬这样的寡妇人家。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苦涩,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梦想。把贫困阴影彻底从历史的天空中驱散是当下全国的目标。精准扶贫全民总动员,黄家义所在的机关单位全体职工都有实打实的结对帮扶任务。黄家义有三户,集中在离县城八十余公里的一个偏僻乡村里。 第一次入户调查时,他先走访了宋依芬之外的两户。很顺利,户主很感激也很配合。可到了宋依芬家则有些“卡壳”。按惯例黄家义先是介绍自己是县上某单位派来的结对帮扶干部,宋依芬出乎意料地说我不当贫苦户,不需要别人的施舍和同情。黄家义无法把话题往下延伸,还好当向导的老金说,依芬,扶贫是国家行动,是实实在在的惠民政策,不是谁施舍谁。宋依芬说,把这种施舍给别家吧,我有脚有手,不想连累国家。黄家义说,扶贫不是给钱给物,是帮你减轻家庭负担,可能的话,想办法找条致富的好路子。 宋依芬说,村上给了我低保就够了,孩子们饿不着,账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的,不会赖。 可按国家脱贫标准,你家还在贫困线下。黄家义说。 宋依芬不再说话,一边搅拌着猪食一边配合着黄家义填入户登记表。 返回单位后黄家义向领导提出换人。他说宋依芬是个寡妇人家,他一个大男人不好做沟通,还是换成女干部合适些。 领导笑着说,老黄同志,你是去帮她家经济上脱贫,不是去结对相亲,你思想上只要不把她往床上扶,工作都好开展。老黄顿时涨红了脸。 三 宋依芬还麻木地守在死骡边上。有两只按耐不住的乌鸦已经站在了骡尸上准备开餐。 依芬,对不起,都怪我。黄家义说。 不怪你,黄哥,是我大意。宋依芬说。 我会买匹骡还你的。黄家义说。买匹比这还壮的。 我不要!宋依芬说。 你先回家,死骡我来处理。黄家义说。 你咋处理?宋依芬说。 老金联系了个收残牛残马的很快过来,两三百块钱还是卖得的。捡回一分是一分。黄家义安慰她。 不卖,我不卖!宋依芬的情绪突然像泄堤的洪水倾泄出来,不管不顾的哭声乍然响起,把死骡身上的乌鸦都吓得惊慌失措地飞起来。 黄家义站在边上不知如何是好。 大约半小时后,宋依芬才止住了哭声。 黄大哥,你忙你的工作去,死骡我会处理。说完她去取了板锄,在死骡边上的地里拼命地挖。黄家义明白了她要做什么,他不敢轻易阻止。 烈日下的宋依芬像疯了一样地挖坑,黄土在她的锄下被迅捷地翻腾起来。黄家义不敢相信一个中年女人身体里居然会爆发出那么多的能量与气力。 埋完死骡,宋依芬跌跌撞撞地回家去了。黄家义站在地里不知所措。烈日炫目,天地一片混沌燥热,他感觉自己像尾挂在竹竿上晾晒的咸鱼,水汽在迅速消散,肉体在快速地风干萎缩。 四 大春种烤烟是滇东地区几十年来的农业传统,也是许多农村家庭最稳定的收入之源。不过种烤烟是个苦活累活,三月育苗,五月移栽,九十月烘烤后出售,每一环节都需要起早贪黑的劳动付出,一个流程结束就是大半年的光阴。 十四年前,宋依芬从邻村嫁给胡二栓后,夫妻俩一直以种烤烟为业。尽管劳作辛苦,但收入不错,日子过得结实丰满。可天有不测风云,婚后第八年的某天,气饱力足的胡二栓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去医院一查却已是肝癌晚期,家里的天空瞬间崩塌。宋依芬不服死神对丈夫的判决,想尽办法去医治。结果是人财两空,没留住丈夫,还欠了亲戚朋友沉重的债。遗产是那栋建好不过一年的二层楼房、一匹老骡和两个嫩娃。这是黄家义结对帮扶后摸查到的宋依芬家的底牌。打铁还要本身硬,这是解决贫困的治本之策。宋依芬有打铁的决心,但没有打铁的资本,但没有资本也必须要打,生活不会放过她。作为土生土长于乡村且独自拉扯着两个嫩娃的女人,她没有其余更能苦钱的路子,只能坚持大春种烤烟,小春种菜籽,以此收入来还债,并勉强解决家人的衣食之需。 平心而论,作为工作近二十年来一直呆在机关办公室、整天只能与材料打交道的结对帮扶干部,黄家义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能立竿见影地帮助宋依芬解决因债致贫的窘境。 黄家义帮扶宋依芬家最大的扶贫工程是果树种植。土地是慈悲的,投之以劳动,假以时日,必定会有硕果回报。作为老家在农村、自小熟悉土地的黄家义始终坚持这一朴素的因果观。为了帮宋依芬家找到条稳定的脱贫增收路,黄家义专门找了县农业局的熟人,请他帮忙申请来了一千棵纸皮核桃苗,并亲自扛锄上山,帮着宋依芬在她家的山地里种下去。保守说,只要成活率有个百分之二三十,五六年后挂果,绝对是笔稳定的收入之源。 另外能帮扶的是些不疼不痒的鸡毛蒜皮之事。譬如宋依芬的孩子到镇上去读中学时,黄家义自告奋勇地去学校找到领导,把孩子分进了一个教师搭配较好的班级。孩子入学报道那天,他主动开着自己的车把孩子送去学校,尽管是辆老掉牙的吉利金刚,还是惹得其他走路去学校的孩子们羡慕妒忌。周末孩子放假时,只要黄家义在村里,他都会主动去把孩子从学校接到村里交给宋依芬。沿途遇到同村的孩子,黄家义会顺便把他们捎回来。 对结对帮扶的另外两户,黄家义一样尽心对待。他以自己的公职名誉为担保,向一家种猪场赊了两头种猪给其中一家饲养,希望借老母猪的肚子繁殖猪仔获取收入,改善贫困。没料想种猪入户才三个月就传来猪“不幸去世”的消息,黄家义忧心忡忡地赶去他家看。户主哭丧着脸说猪得病死了。黄家义问病猪咋处理的,户主不以为然地说,当然只能吃了它。细心的黄家义在他家房门背后,发现了吃剩下腌在锅里的猪头猪腿。他有些怒不可遏,但却不好发作。赊着的种猪钱肯定只能由自己承担。另外一户黄家义实在找不到帮扶路径——七十多岁、弓腰驼背、耳聋眼花的老两口和一个五十多岁、智力有严重障碍的光棍儿子构成的三口之家,住房破旧,家徒四壁,毫无劳力,每天只会蹲在墙根下晒太阳、看蚂蚁。多年来一直享受低保。黄家义结对帮扶后,只能依据相关规定,兜底扶贫。为他家争取了免费住房款,由村委会统一聘请工程队建好住房,算是住有所居。逢年过节时,黄家义用自己的工资买些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生活必须品送去,权当救济帮扶。 五 宋依芬没来找黄家义,倒是胡大栓来了。在村委会里,当着老金几个干部的面,胡大栓问,黄干部,我弟媳家的骡死了咋办?地里的活离不开牲口。 黄家义说,这是偶然事故,错不在我吧? 胡大栓说,骡就是因为吃了你送去化肥死的,你说与你无关么? 老金听了胡大栓的话有些生气说,大栓你狗日的是杀人不怪人怪刀噶!是依芬大意犯了错,你却要赖人家黄干部。 胡大栓说,我不管,反正骡就是吃了他买的化肥中毒死的,二者有联系。 老金说,你这是无理取闹。再说依芬都承认是她的错,你来这里凑哪家灶里的火? 胡大栓说,我兄弟死的早,我是他哥,肯定要为她做主。 老金说,你别闹了,先回去,这是涉及到扶贫户家的大事情,村委会不会不管,容我们商量商量。 胡大栓说,烤烟这几天正是中耕关键期,等商量好么黄花菜怕都凉了。 老金说,你家的骡先借依芬家用一下嘛,我们尽快想办法。 胡大栓说,一匹骡干两家活,换成你家牲口咯舍得?再说我还不是建档立卡户,出不起骡料费。 她不是你弟媳么?咋算的这么精!老金说。 亲兄弟,明算账。我又不是旧社会的地主老财。胡大栓说。 不要你操闲心,她家地里的活,我会帮她干。黄家义说。 那我倒要擦亮眼睛等的瞧。胡大栓冷笑着走出了村委会。 六 胡大栓前脚离开村委会,乡上联系分管村委会的副乡长张琛后脚就来了。 老金,宋依芬家的骡死了是咋回事?还没坐下来,张琛就问老金。 你咋知道?老金觉得这消息也太特么传得快! 她家今年是脱贫出列户,大牲口是计算在内的,半个月后市里的验收组就要下来,万一查到她家咋办?张琛说。 现在是农忙风口上,没有大牲口,她家地里的活咋整?张琛接着说。 我也在考虑。老金附和说。 走,去她家看看!张琛屁股还没沾热凳子就叫上村委会一干人去宋依芬家。 宋依芬家和胡大栓家的住房是紧挨着的,宋依芬家是楼房,胡大栓家还是破旧的土坯房,中间有个低矮的石墙做分割。沿石墙根部的花台里种满了火棘——当地人俗称“救军粮”,一种带刺的天然防护栏。七八月间挂满通红如火的果实,味道酸甜可口,只是摘的时候如果不留意,就会被尖锐的硬刺扎伤。 看一个院落就能看出这个家里有个什么样的女人。这是个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尽管养着猪鸡牛马等牲口,可地板上看不到一块粪便,院里闻不到一丝牲口的臭味。院里有两棵枝繁叶茂的八月桂,顺墙根一溜儿是石砌花台,里面种着月季、绣球、海棠、串串红、灯笼花。院墙上爬满素馨花蔓,每到花季,小院里一片芳香。当初老房子里遗留下来的石缸也被她搬到院里,并且在缸里倒了泥,插了两茎藕。黄家义是两年前荷花开得最好的时节第一次入她家做扶贫调查的。他根本不相信这个家庭会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可事实就是如此——因为男主人患病而不得不背负的沉重债务把这个本来幸福美满的家庭推进了贫困的泥潭。黄家义通过与自己挂钩结对的另外两户贫苦户以及他走访过的村里的其他贫困户相比得出这样一个简单而朴素的认识:一个家庭的贫困,除了天灾人祸不可抗拒,老弱病残无法改变的客观原因外,最大的原因来自于家庭成员的“精神贫困”——那些好吃懒做,不务正业、不思进取、只想等靠要的人,贫困是注定的。富裕生活绝不会从天儿降,“勤劳人家早致富”是个亘古之理。 宋依芬家的贫困是暂时的贫困。这一点黄家义深信不疑。可眼下,厄运之神实在有些无耻与残酷,不断吞吐着阴霾步步紧逼。 七 宋依芬家的院门是半开着的。张琛带着一群人轻易就走到了场院里。院落里躺着一条和气的老黄狗,见有人来站起来摇摇尾巴后接着躺下睡觉。 依芬,依芬,咯在家?老金朝着堂屋里吆喝。 没有应答声但是门打开了,宋依芬无声地站在门里。 依芬你不要急,骡死了我们会帮你想办法。张琛开门见山不婉转。 依芬,这是我们乡上的张副乡长,特意来你家了解了解情况。老金补充了一句。 你们稍等下。宋依芬转身进屋去了,三五分钟后她把大门拉开了,淡淡地招呼一群人进屋坐。黄家义猜想她刚刚消失的原因肯定是去擦干脸上的泪痕并整理了散乱的头发。她家里简单到没有电视,没有沙发,只有几个木板凳,但是整个堂屋却是异常的干净整洁,几乎看不到苍蝇飞动,这在农村家庭中实在是个奇迹。 依芬你也不要太难过。保重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张琛说。 嗯,我晓得。宋依芬小声应了一声。 骡死了是个意外事件,你也不要怪其他人。副主任张晓光插了一句。 不怪别人,都怪我,是我不中用,连个牲口都看不好。一提到骡子的死,宋依芬的情绪一下子又落了下去。 人家依芬通情达理,咋会怪别人?老金赶紧纠正张晓光的话。 依芬你放心,我会买匹骡还你的。黄家义再次重复自己的承诺。 不要!我不要!骡太贵!我担待不起。宋依芬说。 没骡你咋运化肥?咋把烤烟拿回烤房?咋去乡上卖烤烟?黄家义说。 先不提这个,张琛转了个弯。可眼下你地里的活路咋整? 我会想办法的。宋依芬说。 要不这样,依芬,烤烟中耕耽搁不得,这几天你先借匹骡帮着把烤烟地里的活整完,接下来我们再想办法。老金提出建议。 嗯,宋依芬低低地应了一声。 靠她去哪家借?老金你想办法,也不白用,村委会想办法补贴点骡料钱。张琛说。 行。老金知道尽管村委会资金很困难,但眼下只能如此。 七月的牲口是三十晚上的砧板,哪家不用?张晓光提醒说。 就借胡大栓家的吧,他们是亲戚,好说话。张琛提建议。 我不要他家的骡。宋依芬坚决否定。 咋啦?依芬,哪家不是一样,骡料钱我们不少他。老金说。 我就是不要他家的骡。宋依芬的口气还是很倔强。 就和大栓商量一下,老金你去说。张琛做了定夺。 宋依芬不再吱声。 八 胡大栓的结对帮扶干部是刘晓展,为了做胡大栓工作,一起和老金去了胡大栓家。 没想到胡大栓一见到刘晓展劈头就问,刘干部,人家黄干部给贫困户送化肥,你咋不给我家送来? 刘晓展心里有些生气,但表面还是笑眯眯地回敬说,我上辈子欠你家化肥噶? 胡大栓说,你们不公平!送她家不送我家。 胡大栓,只要你能扛着锄头去地里干一天活,我就送你一袋肥!刘晓展将了他一军。 胡大栓狡黠地说,你先把化肥折算成钱给我我就去! 你狗日的不害臊,人家刘干部不欠你。老金阻止了胡大栓的无赖要求。把话题转到借骡的事情上。不过不顺利。因为在村委会和黄家义有过赌气话,老金一开口,胡大栓就飚风凉话。 老金只好耐着性子做工作。可胡大栓提出的条件把老金激怒了,他除了要双倍的骡料钱外,还要为自己家要个免费建房名额。老金说,不合条件怎么给你?胡大栓说,你是村主任,你说了谁敢不给? 放你娘的骡屁!老金火了,抬起话就骂胡大栓。可胡大栓一点不恼,还是笑嘻嘻地说,那骡的事我不敢答应你。 离开你胡屠夫,难道老子就吃混毛猪!老金和刘晓展一怒之下甩门而去。 九 黄家义一大早就来到宋依芬家门前。可她家的大门是紧闭着的,黄家义喊了多声也没有回应,遇到个过路的村民说刚刚看见她上山去了。黄家义立即向她家地里赶。 宋依芬家的承包地在村后的一个山坳里,需要翻山下坎。可能因为背着沉重的肥料,在村背后的半山坡上,黄家义看见了一个背影沉重的女人在使劲地爬坡。他快速地追上,并去抢宋依芬背上的篮。 黄哥,你是公家人,爬山你不如我,宋依芬气喘吁吁地拒绝,汗水把头发浸湿了贴在脸上。 我也是个农村人,干农活比你在行。黄家义背上了沉重的篮筐鼓足干劲朝前走,宋依芬只好扛着锄头跟在后面。 山里的清晨很凉爽,空气中有股甜丝丝的味道,早起的鸟儿们叽叽咋咋地在林间喧闹,它们不懂得人间的艰辛与苦难。 黄哥,拖累你了,有我这样不争气的联系户。宋依芬说。 别这样说,依芬,你是好样的,我没见过你这样有骨气的联系户。黄家义说。 你夸我。宋依芬有些不好意思。 没有,真的。黄家义说。 黄哥,以后你别来帮我,省的别人嚼舌根羞辱你。宋依芬说。 我不怕,你是我的结对户,这是我的任务。黄家义说。 我是个寡妇,你不怕家里大嫂多心么?宋依芬说。 嘿!这个……黄家义欲言又止。 十 端午前后是烤烟与杂草共同疯长的季节,除草留烟并追肥是烤烟中耕期的关键,必须尽早完成。今年宋依芬有些不顾实际地把自家的四五亩地全种了烤烟,劳作的艰辛可想而知。到了地里,两人不敢休息就忙开了,宋依芬拔草施肥,黄家义翻垄清沟。雨水季节已经来临,烟垄必须培土,烟沟必须清理通畅,要不山水一漫就会泡坏烟苗。岁月不饶人真他奶奶是个真理。尽管黄家义来自农村,从小没少干过农活,但毕竟不稼不穑接近三十年,重新抄锄劳动是有些吃不消。更何况天气炎热,三五墒锄下来,浑身的衣服就湿透了。他只好跌坐在地埂上稍作休息。宋依芬看见了,走过来歉意地要他回去休息。黄家义说,开工没有回头箭,你不要纵容我当逃兵。再说,劳动是锻炼身体的最好方式,要不骨头都要闲了生蛆了。宋依芬看着黄家义,眼里突然有了亮晶晶的东西要滚落下来。 黄哥,联系我这样的人家,你怕是我们县里最遭罪的扶贫干部。她说。 我是完全自愿的,绝不悔意。黄家义玩笑般地扬起拳头向宋依芬 宣誓。 你先休息下,黄哥,化肥完了,我再回去背一袋来。宋依芬说。 路太远,你背不动,还是我去吧。黄家义说。 你不熟悉路,还是我去。宋依芬说。 黄家义不好再坚持,只好任由着宋依芬去了。点燃一支烟,看着艰难的山路,黄家义再次感受到大牲口对山里农户的重要性。 胡大栓这时出现了,牵着他家的骡朝山上来。看那状态不是下地干活,是来溜骡吃草的。黄家义听刘晓展抱怨过,胡大栓之所以也是建档立卡户,原因就是个懒,家里有田有地却是闲荒着的,家里四口人全靠领低保为生。当初兄弟俩分家时各分了一匹骡,是他家最值钱的东西,没事去放骡是他的主要工作。骡倒是养得架大膘壮,可却没有把牲口用到该使力的地方。 哟,黄干部,真来给我弟媳家当骡子使了。胡大栓一脸的幸灾乐祸。 黄家义懒得理他,继续忙着锄草。 好好干,好好干,扶贫工作干不好,头上的乌纱帽是要被摘掉的。在胡大栓心里,他完全把扶贫当做是干部们升迁的例行公事。 黄家义一下子为他这种无耻的话激起起怒火,但他还是压住了,继续不理他。 胡大栓感觉很无趣,牵着骡走了。 宋依芬回去了大半天还没有来,正午的太阳热力再加上腹中的饥饿让黄家义彻底放弃了劳动,坐在地边的一棵冬瓜树下休息。这时他放在地埂上的手机突然响了,拿起一看是刘晓展打的。刘晓展说宋依芬背着化肥昏倒在了出村的路上,被村民遇到后送到了卫生室,让他把地里的工具带回来。黄家义有些意想不到。电话里不好细问,连忙收拾了劳动家什,直奔村卫生室。 宋依芬正躺在卫生室里打点滴,村医说是长期劳累过度导致低血糖昏迷,输点液就会慢慢缓过来。此时的这个女人不再倔强,安静地闭着眼睛。黄家义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工作关系,黄家义和她熟识近三年了,不过黄家义从来没有、也不敢过多地盯着她看过,此时,趁她闭着眼睛熟睡之机,他才敢大胆地、细细地打量她。说句世俗的男人话,宋依芬这个比他小两岁的女人绝对算得上是个美丽女人,若不是因为生长在这穷乡僻壤且被厄运之霾笼罩,岁月与生活的沉重担子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一定不甘心隐藏自己的天生丽质,她一定会在村庄中开放得灿灿烂烂,绝不逊色于城市中任何一个漂亮女人。 在村卫生室里还有一个特殊的伴护——宋依芬家里的那条老黄狗,不知何时进来的,安静地躺在宋依芬床下的鞋子边,黄家义低头看狗的时候狗也看他,大狗的眼里饱含泪水,他的心里禁不住颤抖了一下。 十一 寡妇门前眼睛多,更何况是个年轻且漂亮的寡妇。中年丧夫的宋依芬在村里是许多年轻媳妇们重点盯防的对象。她们严防自己的丈夫接触她,甚至不允许自己的丈夫单独从他家门前经过。宋依芬从她们的眼里看到的是戒备和怀疑之光。在把宋依芬划进贫苦户行列的事情上,她们在背后总有非议,尽管她们心里清楚,这是毫无根据的怀疑和中伤。她们这样议论的目的只有一个,尽量防止自己的男人有非分之想。宋依芬很知趣,绝不轻易和村里的男人们接触,一个人小心地规避着那些摆不脱的俗世镣铐。上门提亲的人不少,多数是邻村的丧偶男人,也有几个大龄的光棍,他们对宋依芬是百分百的满意,可一听到她家欠着的债务和两个半大的孩子就打了退堂鼓。再从宋依芬这里来说,有几次提亲是她主动拒绝的,她说自家的负担重,不想拖累别人。 花香总会吸引蜂蝶。宋依芬感受得到,一个人上山干活或行走在村路上,总会有些异样的眼睛在偷偷地扫描她。有些像牛对青草的期盼与眷恋,有些像饿狼般的饥饿与放肆。最让她恐惧与不安的是半夜里,有些醉汉们会趁着酒兴来敲她家的门,并放肆地说些毫无遮拦的话。宋依芬无法摆脱这些无耻的纠缠与骚扰,她只能牢牢地关好自家的门,小心翼翼地坚守着自己的城池。 百密总难免有一疏。今年惊蛰时节的一个夜里,在村委会宿舍熟睡的黄家义突然被急促的手机铃声惊醒,拿起一看居然是宋依芬打的。他立马有些紧张,快速接通后却听到宋依芬没有对着电话说话,而是在免提状态下大声地叱喝某个出现在她面前的男人。“你要干什么,你赶紧滚出去!”男人有些恼怒地说:“宋依芬,你是我兄弟媳妇,就永远是我胡家的女人,我想怎样就怎样!”“呸,二拴有你这样的哥是作孽!”宋依芬电话那头很紧张,但语气很坚硬。来不及多想,黄家义抓了裤子飞速地穿上就飞跑向宋依芬家。平时要走十来分钟的村路他三四分钟就赶到门前,直接一脚飞踹就把结实的院门踢开了冲进去。或许是听到了院门崩开的响亮声音,屋内的男人像野狗一样窜出来,敏捷地翻过低矮的隔墙跑了。 里屋的宋依芬右手拿着剪刀,左手拿着手机,靠在墙根紧张成一尊根基不稳、摇摇欲倒的雕塑。 我报警抓了这狗日的!黄家义恨恨地说。 别,别,别,黄哥!宋依芬颤抖着阻止黄家义。 依芬,你不能太软弱,饶过这狗日的他还会作恶。黄家义的愤怒之火还在头上。 都怪我大意,忘了把门锁扭横。宋依芬抬头看着黄家义,突然又惊慌地转过身去。 黄家义怔了一下才发现自己来得太急,只忙着抓了裤子穿上,却忘了穿衣服,还赤裸着上身。这大半夜黑咕隆咚的以这种造型出现在一个寡妇家里,警察来了怎么解释?要是第二天村民们谈论起此事,会怎样猜想议论? 依芬你把门关牢了。别怕,有事就打电话给我,我是你的帮扶干部。黄家义不敢久留,留下句苍白无力的安慰话后赶紧离开了宋依芬家,悄悄地折返回宿舍继续睡觉。 十二 两天后的中午时分,副乡长张琛又赶到了村委会,召集了村两委班子和驻村扶贫工作队全体成员开会。他先是宏观的讲了近期扶贫工作的总体要求,特别提出要大家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准备迎接几天后省里派来的脱贫攻坚验收。接着详细讨论分析可能存在的“工作短板”,宋依芬家依然是绕不开的坎。 张晓光说,宋依芬是个集体荣誉感很强的女人,事先提醒她不要说家里骡死的事情,就说被娘家借去用几天。先把检查组应付过去。 黄家义不同意张晓光的意见,他说检查固然是大事,关键现在她地里的烤烟活路咋整?现在又生病,大牲口又死掉,靠她一个女人咋完成?时间不等人,中耕期管理不好烤烟就黄了,烤烟黄了全年的收入就黄了,收入黄了她家日子咋过? 老金说,是必须要想办法给她家添头大牲口,要不往后的活路没法干。 张琛叹口气说,这事我已向书记作了汇报。可乡里没有这类特殊补偿金啊。 不消,我一定买匹骡给她,帮她忙完这几天我就去买。黄家义说。 老黄,别讲赌气话!这骡的死和你没半毛钱的关系。没有谁怪你,你别往自己身上揽责任。老金说。 一匹壮骡七八千块下不来,不是小数目。你那点工资养家糊口也不容易,咋能让英雄流汗又流血。张琛说。 再说依芬人穷志不短,她咋会接受你的这大笔礼物。张晓光说。 这事就这么定了。请大家相信我。黄家义不容置否地说。 会后形成的决议是村委干部和驻村扶贫工作队成员第二天集体劳动,先帮宋依芬家完成烤烟地里必须的活。 不过当这支临时组建的“助贫劳动小分队”一大早到达了宋依芬家地里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匪夷所思的情况——宋依芬家的烟地已然被深谙农事的人认真地收拾过了!草被锄得干干净净,垄土被翻过,垄沟被理过,一株株茁壮的烟苗正在清风雨露里欢快生长! 是谁干的?张晓光问出了大家心里共同的疑问。 依芬这么好的女人,背后肯定有很多人在惦记她。老金冒出了一句曲折婉转的话。 十三 七月的天,孩娃的脸,天气是说变就变。午饭时分,村委会一干人端起碗的时候天空中是没有乌云的,可吃完后到院子里一看,急促的乌云就从四围的山顶上快速地涌泻出来,还伴有惊魂不定的乱风,吹得院里的板栗树不知所措地摇晃。这时老金接到张琛的紧急电话说,气象台打电话通知,十三点左右将有场暴风雨来临,村委会要做好应急准备,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要重点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uanshens.com/wssgn/6144.html
- 上一篇文章: 中医怎么看待类风湿关节炎有没有简单实用
- 下一篇文章: 隆力奇牌纯蛇粉胶囊的功效